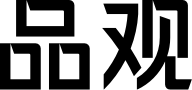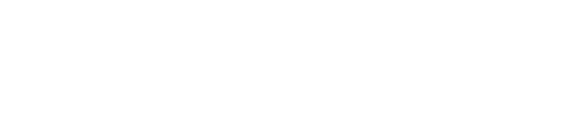进入中国将近30年的屈臣氏因彩妆经营不善一直饱受诟病。
财报显示,屈臣氏2016年老店同比上一年下降10%,2017年上半年同比2016年上半年下降6.2%。面对可比门店生意下滑的重压和彩妆在中国的井喷增长,过去一年里,屈臣氏开始拿彩妆开刀。
屈臣氏从2017年的第八代店铺开始推行New Trail(新模式),将此前全国400多个品牌彩妆专柜撤柜,改为Makeup Studio(彩妆体验中心)和Cosmetics Wall(靠墙背柜)。不料,突然性调整直接导致彩妆品类可比门店同样下滑严重,而New Trail的店铺销售远不能填补专柜生意下滑的缺口。
曾在美宝莲任职过的知情人士向品观网(pinguan.com)透露,当前屈臣氏的彩妆品类销售占比已下滑至10%左右,不及CS渠道的平均值,也不及调整之前的占比。
面对日益兴起的彩妆,屈臣氏为何始终难掩尴尬?
不重视彩妆销售
“丝芙兰可不是因为店铺豪华、大品牌多才把彩妆做成了核心品类,她与百货的品牌重合度很高,能活到今天,靠的是调性来聚客,专业来转化。”一位浸淫行业多年的上游供应商跟记者持相同的观点,彩妆师、彩妆BA的化妆技能与服务能力是经营彩妆的核心要素,这也是近些年本土CS店彩妆占比得到提升的根本。
简而言之,在中国卖彩妆离不开人。但屈臣氏恰恰背离了这一点。
在第八代店铺推出之前,除了美宝莲等少数几个彩妆专柜外,屈臣氏的彩妆大多是以中岛开架分散陈列的,且产品不够集中,这种陈列方式更适合彩妆消费成熟的市场和店铺,但屈臣氏甚至没有为这些区域配置彩妆BA。
你走到开架彩妆区,却发现没有BA主动上前。面对类似的尴尬,顾客只能猜测,屈臣氏不卖彩妆或者屈臣氏的BA不懂彩妆。

还有一种场景也是消费者时常遇到的。因为屈臣氏没有培养自己的彩妆BA团队,其彩妆运营分品牌操作,每一个入驻品牌都有自己的专职BA,因此常常会发生,某彩妆专柜空无一人的时候,隔壁的彩妆BA宁愿聊天也不过来给顾客服务。
从BA的懈怠可以窥见屈臣氏对彩妆的态度。事实上,在2016年中第七代店铺推出以前,屈臣氏并没有真正意义的彩妆体验区和试妆台,过去二十多年里这家巨头连锁未曾强调过用彩妆跟顾客沟通。
试想,通过BA的推销能把自有品牌卖到全年销售额排名第一的屈臣氏,为什么卖不动彩妆?根本原因实则是战略上的不重视,管理层的态度直接酿成了今天的结局。因而屈臣氏经常被同行戏称“没有彩妆基因”。

供应商不愿用护肤贸易条款卖彩妆
2017年上半年屈臣氏中国的EBITDA (指税息折旧与摊销前利润)毛利率是21%,仅比2016年全年下降1%,大幅领先全球其他市场,屈臣氏东南亚门店的EBITDA是14%,欧洲是7%。业内某零售专家认为,这个数字高得太离谱。
因屈臣氏中国一直未下调与EBITDA有关的关键业绩指标,导致采购部门在与该项指标密切相关的毛利率和OI(屈臣氏向供应商收费的统称)两块主要收入上均无下调空间,在此重压之下,采购部不得不将压力转嫁给供应商。
供应商除了要给到屈臣氏至少30%(30%-38%)以上的毛利率外,还需要承担名目繁多的OI费用与BA人员费用,因而出现做多亏多的结构性亏损,最终进入恶性循环。

一位接近屈臣氏的同行告诉品观网(pinguan.com),屈臣氏的贸易合作条款十分苛刻,主要涵盖折扣项目与退佣,屈臣氏为供应商提供的业务推广服务费两大板块,这些费用统称OI。描述更详细点就是,屈臣氏会向供应商收取节庆促销服务费、BA费用(供应商派驻的BA要缴纳BA管理费)、DM宣传海报费和DC仓物流费。
比较不可思议的是,在屈臣氏与供应商签订的贸易条款里,每年的屈臣氏周年庆、春节、妇女节、劳动节、国庆节、圣诞节等节庆,供应商都要向屈臣氏交纳数额不等的固定费用,最少不低于500元,最高的比如三八妇女节高达15000元。
在这些种类繁多的OI费用当中,DM海报费是最贵的,其中单图海报费是1万元左右,半个版面则高达5万多元。
“屈臣氏跟所有供应商合作都是用这个贸易条款,彩妆品类也不例外。”曾在知名一线彩妆品牌供职且与屈臣氏有过生意往来的某知情人士表示,屈臣氏用做护肤的生意条款来运营彩妆是不合理的。众所周知,彩妆在中国还属于市场培育期,需要更多的人力和物力投入,按照屈臣氏的这项贸易条款,彩妆品牌需要承担过重的运营成本,力不从心。
正因为这样,很多彩妆品牌有些“忌讳”进屈臣氏。根据此前我们的报道,本土品牌蓝秀曾接到过屈臣氏的邀请,但基于运营成本过高和严苛的合作条款,蓝秀总经理张子龙最终舍弃了屈臣氏。
产品不丰满,品牌结构缺乏吸引力
在第七代门店推出以前,中国2600多家屈臣氏拥有的彩妆供应商包括美宝莲、凯朵(KATE)、姬芮(Za)、卡姿兰、兰瑟、猫语玫瑰和玻儿,外加自有彩妆骨胶原系列、Makeup Miracle和My Party Gal等。
但实际具体到每一家店,屈臣氏的彩妆陈列面积极其有限,比如位于武汉京汉大道大润发的屈臣氏门店,只有兰瑟和美宝莲2个品牌专柜,对于进店顾客而言,几乎感受不到任何彩妆氛围。另外在一些面积更小的屈臣氏店铺,甚至一个彩妆专柜也没有。

不得不说的是,屈臣氏还错过了韩系彩妆最火的黄金时间。从店铺定位来看,价格亲民、形象突出,且善于做营销的韩国彩妆对屈臣氏来说是再合适不过了。
可惜的是,早前被本土CS店卖爆的爱丽(已改名为伊蒂之屋),以及被网络炒红的3CE等品牌,因个中缘由都没有入驻屈臣氏。
错失韩系彩妆快速发展期的屈臣氏,在2017年主动调整了彩妆品牌结构,推行国际化策略,尤其以日韩进口品为主。首先引进了CLIO(珂莱欧)、I’M MEME、peripera(菲丽菲拉)、the SAEM(得鲜)、KISS ME等品牌;同时减少了部分原有的本土品牌进店数量,其中卡姿兰、兰瑟、猫语玫瑰等品牌的进店数量均有所缩减。

知情人透露,卡姿兰和兰瑟等品牌的逐步退出,实际与品牌销售增长未达预期,盈利不佳有直接关系。代替本土品牌站队的是玛丽黛佳,但据了解,玛丽黛佳仅入驻了第八代门店和华南区个别门店。
虽然屈臣氏在今年引进了日韩主流彩妆品牌,但上文中接近屈臣氏的同行认为,一方面时间太晚,另一方面这些品牌在屈臣氏均无独家销售系列,与其他渠道相比,屈臣氏仍处于劣势。

“彩妆销售对BA的终端拦截非常依赖,虽然屈臣氏引进了这些品牌,但缺乏专业BA,所以到目前为止,多数品牌的单产比较低。”据另一位知情人透露,被屈臣氏重点推介的CLIO(珂莱欧)的销售也未达预期。
还有最新消息称,屈臣氏直采的CLIO(珂莱欧)原本由上海月沣团队运营,但不久前月沣已退出CLIO的品牌运营。不知这对屈臣氏来说是否是一个噩耗?
还需要补充说明的是,受2016年、2017年集团财报下滑影响,屈臣氏彩妆品类的第一大客户——欧莱雅集团正在减少对屈臣氏渠道的投入,其中美宝莲品牌撤掉了相当数量的不盈利的专柜,由此给屈臣氏的彩妆带来了阶段性下滑。可以想见,那些没有了彩妆“杠把子”美宝莲助力的屈臣氏店铺,彩妆会不会更难卖?
彩妆BA缺培训,终端运营成痛点
屈臣氏第八代店铺的空间设计和整体视觉都得到了全面升级,其中彩妆板块变化最大,氛围营造也有较大的提升。为了能卖好彩妆,屈臣氏还启用了智能彩妆模拟试妆设备STYLE ME。

但为什么试行了近半年,屈臣氏的彩妆占比不升反降呢?根本原因在于缺少专业能力足够强的彩妆BA。
决心在彩妆上发力的屈臣氏也意识到了人的重要性。于是从第七代、第八代店铺开始大规模取消了供应商专职BA(自有品牌BA除外),改变了各自为阵的状态,调整为Share BA(自己招聘BA)。

不过由于内部体系太庞大,Share BA项目最终由采购部、营运部和HR(人力资源部)三方合作推进(在屈臣氏,采购部负责向供应商收取费用、HR负责招聘、营运部做日常管理)。
Share BA的主要来源分三块,一是原专柜品牌撤场后,BA就地转给屈臣氏,以美宝莲、ZA和KATE居多;其次是由屈臣氏HR主导在各地美容美妆专业院校招募95后应届毕业生,而且屈臣氏还提出要大范围扩招男BA;三是由屈臣氏营运部面向社会招聘。
但结果很不理想,专柜BA转岗后出现品牌销售不均衡的问题;95后应届毕业生因缺乏培训、产品知识欠缺难以转化,招聘男BA的愿望更是因一些客观原因没有实现;而面向社会招聘的BA甚至出现了年近50岁高龄。
“我7月底在北京逛屈臣氏的时候看到一位50多岁的大妈,这在彩妆领域是难以想象的。试想一下,有哪个消费者愿意去这样的店铺购买彩妆?”烟台恒美总经理孙锡财断定,屈臣氏基本没有彩妆基因,提升彩妆占比不是一朝一夕能实现的。

Share BA的整体质量之所以差,根本原因是因为屈臣氏的BA培训存在绝对的短板。
入驻屈臣氏的某彩妆品牌透露,因屈臣氏自身的培训体系尚未搭建完,Share Ba的培训目前均由供应商派驻培训老师进行现场集中式培训,但因Share BA的流失率过高,直接导致培训的有效性大幅降低。一环扣一环,最终的结果是,屈臣氏的彩妆销售也呈直线下滑。
综上所述,虽然屈臣氏雄心万丈,但其彩妆经营之路将会无比漫长。